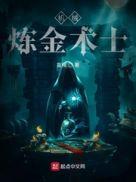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带上系统整顿大理寺 > 第113章(第2页)
第113章(第2页)
这孩子也算自己看着长大的,每次受重伤也都是自己为他医治,治伤时就跟睡着一样,从不乱动也不抱怨,可以说是最让人喜欢的一类病人了。可唯有一点,那就是他从不遵循医嘱,治疗后也毫不顾忌地跟随铁翼骑办案,若不是仗着身体好,早就落下病根了。
见他在岑晚面前难得的乖巧,鲁神医忍不住落井下石道:“去年你腹部中箭,结果我刚给你上好药,第二天就又跑出去追什么采花贼,伤口崩开不敢来找我,还是你下属来偷偷请我过去的!”
岑晚听罢,一双猫眼瞪得老大,盯着薛寒星心虚的脸,仿佛在无声质问:还有这种事?
薛寒星小声为自己辩解道:“只是正巧碰到了,我不能不管吧……”
在岑晚的视线中,声音逐渐变小,很快消失。
“神医您放心,我这段时间会好好看住他的。”
老人呵呵笑了两声,拿起小剪子将那最后一针后多余的线头剪去,道:“恐怕这小子这段时间也会把你看得死死的。”
接着鲁神医留下一罐去腐生肌的药膏,事了拂衣去,留下岑晚与薛寒星面面相觑。
空气有些似懂非懂的、丝丝缕缕的缭绕,这感觉其实不是岑晚第一次体会到,但他总是下意识地回避,不愿意细想。
“你休息会儿,我先出去了。”
可那只一直轻轻搭在岑晚手臂上骨节分明的手却骤然收紧,“我疼,睡不着。”
原本已经直起身打算离开的岑晚又泄了气,“你趴下来,我给你上药。”
薛寒星顺从地趴在榻上,任人宰割的样子。
莫名地心慌让岑晚不知所措,这时候没什么是比案子更能将他从这难受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于是他手中抹着药,又开始和薛寒星他继续聊起案子的事。
听到他们借宿的此地正是死者孙富的家,薛寒星也觉得很是凑巧。
“一会儿我去向她打听一下孙富的事,等咱们走了再派人来通知她丈夫的死讯吧。”
这并非岑晚不近人情,而是现代办案时也会经常采取的一种方案,由于家属在得知噩耗时往往过于激动,在悲伤的冲击下往往难以很好回忆起有用的线索,故而很多时候会先隐瞒被害者的死讯,而先对家属进行询问。
说着说着,话题又到了今天这场莫名其妙的刺杀上。
“那头领的身份不简单,我也没能看破。”
“没关系,若我没有看错,那与我缠斗的人里有一个使的是金蛇剑法,这是金蛇宗的独门秘籍,而能到他那种水平的,非掌门亲传弟子或几位长老不可,明天我就去会会金蛇宗掌门。”
这人是真没记性,岑晚手上涂抹的力道不自觉加重,不再说话,薛寒星也意识到自己失言,马上找补道:“我带人一起去,一定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