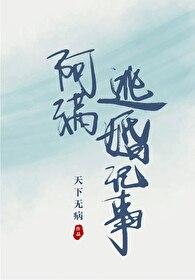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妖怪夫妇探案日常 > 第126章(第1页)
第126章(第1页)
越千城冲他笑,“你说是就是吧。”燕归城城主一时不晓得该说什么——这孩子,爹还能乱认嘛!那他八成就是越斐文的儿子了。看着面孔年轻的越千城他们,燕归城城主再度感慨万端道:“后生可畏啊,咱们这代人会渐渐老去,皇朝能走多远,还是要看你们这群年轻人。”他叫来门口的衙役,吩咐了几句,不多时,衙役捧着一个托盘回来。托盘里面,是晃花眼睛的白银。“你们合力破了这桩多年前的悬案,依照衙门当初定下的赏额,这一百两银子是你们应得的。”燕归城城主大方道:“拿去吧。”霍嘉龇着牙花子从衙役手中接过盛放银子的托盘,沉甸甸的银子到手,他的心情才变好。不赖,加上鸡贼如汀留下的首饰,此趟收获颇丰,够他们敞开腰包耍半年了。无仙派即将从入不敷出走向盆满钵满。从燕归城的衙门出来已是午后,太阳爬到天幕另一侧,空气中弥漫着春日特有的暖湿。路过菜市场,霍嘉下车买了不少好菜,还买了一坛子好酒,准备回无仙派好生吃喝一顿。马车驶过除夜街,车轱辘晃晃悠悠,不停发出快要散架的“咯吱”声。越千城发现,马车刚驶进除夜街,花涴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不对劲。除夜街不是主街,用不着经常反对街面进行改造提升,这么多过去了,它没什么变化,仍和记忆中一样,古香古色,带着前朝古朴的气息。越千城温柔询问花涴,“怎么了?看你的脸色不大对劲。”花涴坐正身子,“想到了一个朋友。”视线在除夜街漫无目的地飘着,一幕幕熟悉的记忆亦从脑海中闪过,她低低道:“他要是活着,估计年纪也同你差不多大了,只可惜……”越千城挑眉,唔,花涴在除夜街还有其他好朋友吗?而且,那个好朋友还死了。他一直以为,凭借花涴当年的作风,除了他之外,再没别的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他追问,“怎么死的?”花涴默了会儿,马车即将驶出除夜街,她回头看了看街角,突然毫无征兆地哭出声音。“呜啊……”越千城顿觉手足无措——他说了什么话,为何花涴突然哭得这样厉害?忙勒住缰绳,把马车停在路边,越千城慌乱安慰花涴,“你、你别哭啊。”他想掏出手帕给花涴擦眼泪,可是摸了半天,兜里什么都没有。他只好捏起一截衣袖,把月白色的衣袖当成手帕,给花涴擦拭眼泪。他用自责来安抚花涴,“你别哭了好不好,全怪我,我不该带你走除夜街的,不该勾起你的伤心回忆。”软软儿的,温柔若月下清泉,叮咚沁入心脾。☆、花涴小时候是个哭包子,打从到山上学艺之后很少再哭泣,可她要是偶尔哭起来,眼泪淌得和小时候一样汹涌,半天都止不住,“不……不怪你,”她拖着浓重的鼻音道:“是我自己心态不好,睹物思人,同你没有关系。”花涴的眼泪真的淌得很多,越千城右边那只衣袖很快便湿了,他又捏起左边衣袖给花涴擦拭眼泪,动作温柔小心,像精心侍弄花草的工匠。花涴便是他手下最满意的一株娇花。“别哭了,”他侧身坐在马车上,柔声哄花涴,“呐,事情憋在心里久了对身子不好,需要找人倾诉。你现在不想说没关系,等以后想说了,可以找我倾诉,我会帮你保守秘密,并且不收任何费用。”少年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花涴微微仰起脸,就着金灿灿的日光望向越千城清澈见底的眼睛,良久,瓮声瓮气地“嗯”了一声。越千城贴心为她擦去眼角滑落的眼泪。霍嘉看不下去了,把车厢的帘子遮好,他堵住耳朵,默默坐到车厢最里面。他一个单身十八年的可怜人,为什么要看到这种画面?等到花涴不再哭泣,越千城重新扬起马鞭,在午后充足的日光中,带着花涴和霍嘉回无仙派。他相信花涴迟早有一日会对他敞开心扉。忙了半日,水喝了一肚子,却没吃半点干粮,晚饭可要多吃些。无仙派的成员们都穷惯了,乍拿到一百两赏金,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想法。吃饭时,白羽生惆怅道:“完了,成暴发户了。”他故作正经地询问大家,“伙计们,你们说我以后该怎么走路,是大摇大摆呢?还是目中无人?”霍嘉亦叹道:“你们说我日后再缺做东西的木头,是花钱找人买呢,还是雇个人拉着斧头去林子里砍?”顾一念跟着道:“那,那我以后上街买菜还讲不讲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