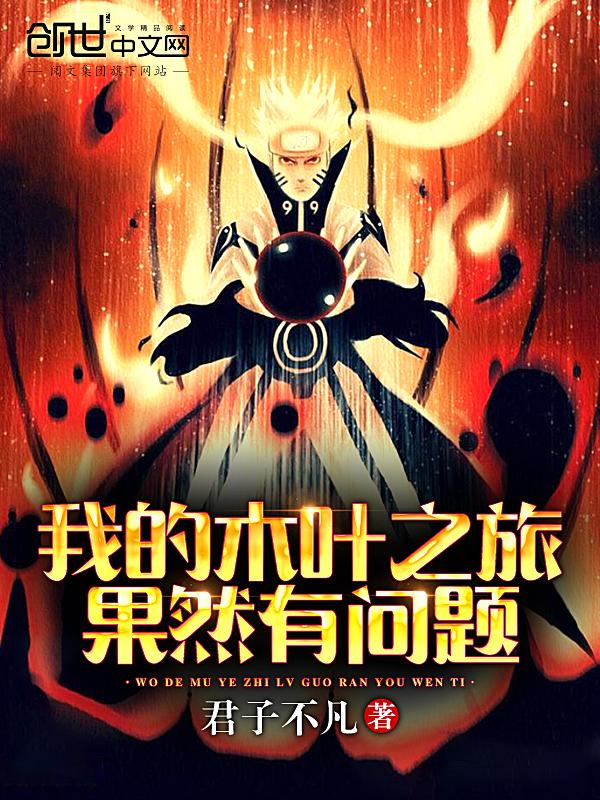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穿越大明,我要逆天改命 > 第2115章(第1页)
第2115章(第1页)
第2115章
朱兴明眼中精光一闪,旋即苦笑:“既如此,朕便直问了——为何加重徭役?朕记得,每年农闲才有徭役的,”
“臣。。。臣实在是有苦难言。”赵德彪从袖中取出本黄绫册子:“这是大名府近五年赋役簿册,请陛下御览。”
朱兴明翻开册子,只见泰康元年栏下朱批"减赋三成",往后几年,赋税逐年递减。
“没错啊,朕不一直都是减免赋税么,”朱兴明奇怪的问。
赵德彪以头触地:“陛下容禀!减赋之后,地方存留税银不足往年六成。可黄河年年泛滥,去岁冲毁堤坝三十余里,淹没良田两万若再不加固,必决口。”
“所以你就只好加重徭役。”朱兴明苦笑。
赵德彪突然跪行数步,有些激动起来:“不加徭役修堤,来年死的人会更多。去年东阿县决口,淹死百姓七百余人,灾后瘟疫又夺去上千条性命啊,臣这是剜肉补疮。”
朱兴明怔住了。他看见赵德彪乌纱帽下露出的白发,官服肘部磨出的毛边,还有案头堆积如山的河工文书。
朱兴明叹了口气:“朕有治理天下的难处,你们也有治理地方的难处。你们,倒是辛苦了。”
赵德彪感恩戴德:“陛下乃是千古不世出的明君,臣等遇到陛下这样的明君,那才是三生有幸,百姓之福。”
朱兴明呵呵的笑着:“百姓之福,朕一路走来。百姓之福没见到多少,百姓之难却是触目惊心。”
赵德彪刚要开口,师爷又来报:“陛下,山东学政胡大人到了。”
“让他进来。”
“遵旨。”
一身脏污的胡善庸拄着竹杖进来,见到朱兴明就要行大礼,被朱兴明制止。
“朕邀你来,正是想让你看看,这百姓服役的事。”
胡善庸这个老学究,似乎是对此早有所料,他看着摊开的赋役册子,长叹一声:“陛下所见徭役之弊,根源在黄河。老臣巡视山东学政二十年,眼见良田变泽国,书院成荒丘。他从怀中取出一卷泛黄的手札,这是老臣记录的历年水患。”
朱兴明展开手札,条目下赫然写着:“六月廿三,寿张决口,溺毙百姓四百余,千里两天淹没。”
“百姓想过好日子,必须开垦农田、兴修水利。”胡善庸的竹杖重重敲在地上:“可这些都要人力物力!衙门拿不出钱,只能征发徭役。。。”
”朝廷不是拨了治河专款。”朱兴明皱眉。
赵德彪苦笑:“去年工部拨付三万两,仅够修补旧堤。若要根治水患,需重建石堤三十里,疏通淤塞河至少五十万两。”
“五十万两?”朱兴明差点跳了起来:“相当于山东一省全年税赋。”
“这还只是应急之需。”胡善庸捋着白须:“若要从根本上治理黄河,需在上游筑坝拦沙,中游拓宽河道,下游开挖引河。这些工程全部完成,需白银更是无数,历时十数载。"
花厅里死一般寂静。朱兴明凝忽然问道:"若只做最紧要的工程呢?"
“那至少需八十万两。”赵德彪立即回应:“可大名府库现存银不足五万两,其中三万还是秋税起运的过路银。”
胡善庸突然咳嗽起来,咳得满脸通红。朱兴明亲自递茶,触到老人冰凉的手指。老学政缓过气来苦笑道:“老臣这把老骨头,怕是等不到黄河治理完成的那日了。”
“胡大人。”赵德彪急忙制止:“您这咳血之症。。。”
朱兴明这才注意到胡善庸袖口沾着暗红血迹,老学政却摆摆手:“无妨。老臣今年六十有三,历任三朝,见过太多治河良策沦为纸上谈兵,陛下可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