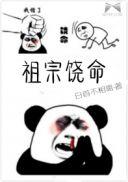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禁止欺负话本女主 > 第306章(第1页)
第306章(第1页)
眼下她情绪不稳定,姜谣只能顺着她,答应,“好,我不会不要你的。”
又听宋暮云声音里带着数不尽的委屈,颤着声道,“谁都可以不要我,但你不行,你不许不要我。”
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想要姜谣,只要她就好。
意思表露的明明白白,但凡对磨镜稍加了解的人,都会起疑心,但姜谣只是心中震惊,她觉得很不对,宋暮云这般说话,很不对,但真要她说她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只是觉得,这是女子对男子才能说出来的话,宋暮云……
怎么总对她说?
一向只看男女话本,单纯无知的二十岁大小姐此时还没学到有关磨镜的知识,自然也没往歪处想,刚觉得不对,又因怀里楚楚可怜,紧紧拽着她袖子无声催促答案的女子而很快接受了。
管她哪奇怪呢,宋暮云在哭,哭的都打嗝儿了,怪叫人心疼的。
“好,不会不要你。”
姜谣答应后就着现在的动作,抱住人家绵软的臀尖,将她抱去床上,又看着她拒绝沾到床,将整个人小猫儿似的缩进她怀里,连带那双白嫩玉足也往她怀里塞。
姜谣蹙眉,这才发现,“你怎么不穿鞋?”
她伸手去摸宋暮云雪白的脚背,上面没什么伤,脉络清晰,皮肉软嫩,触手冰凉。
“寒气都是从脚底进去的你不知道?下次再急也要穿上鞋才许下床。”
她心中格外见不得宋暮云不在意自己身体的样子。
屋内打扫的很干净,宋暮云即便赤足乱跑了一阵,也没沾染到什么泥灰,双足在姜谣手里显得白白嫩嫩的。
但人被训了,就垂着脑袋蔫巴巴,心虚不敢说话。
姜谣托着那只脚皱眉,吩咐人打了一盆水来,后将帕子打湿,再拧干水,亲自替她擦去上头看不见的粉尘。
一双白嫩玉足被擦的湿润润,干净极了,但脚尖也水浸的愈加冰凉,姜谣揉了一把,便手动将人塞进厚实的被窝里,不管她双手抗拒的推着她。
宋暮云没办法,只能拖着被子往姜谣身边抬屁股,又坚强的靠在姜谣肩上。
姜谣见她还有些做噩梦后的害怕神色,便没再拒绝她,反手将她连人带被拥在怀里,轻拍着肩背安抚,“怕什么,你醒来不是看见我在这了吗,我没有走,更没有不要你,好了,不哭了,嗯?”
姜谣摸摸宋暮云软嫩的脸颊,将上面眼泪留下的水痕都擦拭干净。
宋暮云吸了吸鼻子,纤长的手指握成拳头,锤了姜谣一下,没什么力道,软的厉害,姜谣怀疑是因为今天雨中洗衣伤了身子,才会这么没力气,还在心中暗暗想着如何给她调理身子,压根没往人家舍不得用力打她的方面去想。
那拳头又被姜谣包在手里,她听见人家抱怨,“谁叫你不在的,我一觉睡醒看不见你,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她现在胆子小的厉害,生怕自己又回了第一世,姜家人被斩首后。
回到那时候有什么意思?
姜谣都不在了,她又要日复一日沉浸在痛苦里,活着就为了杀慕容清,偏他当了皇上,难杀的厉害,一次又一次失败,日子当真是没意思极了。
宋暮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
她依靠在姜谣怀里,耳边是她强劲有力的心跳声,一颗飘荡不安的心,此时终于稳稳落了下去。
姜谣不懂她有什么好害怕的,但还是耐下心与她解释,“我就在里面沐浴,这次许是洗的久了一点,抱歉,我下次会早些出来的。”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总之看见宋暮云哭,看见她难过,她就觉得是她错了。
赶紧把人哄哄好,如今宋姑娘身子弱,可不能这么哭下去。
然她都道歉了,宋暮云依旧不依不饶,先是带着被子在姜谣怀里扭动着蹭了几下,拉出又长又娇的气音,然后提出要求,“不成,我下次要坐在外头陪你洗,万一你洗着洗着不见了怎么办?”
她抬头,那双漂亮的眼睛清澈见底,竟带着些许忧思,好像真是这样想的。
若说这话的人是姜淮,姜谣只会叫他别发癫,可偏偏是宋暮云说的。
对着一个清雅的小姑娘,好些话她便不忍说出口,顿了顿,神情越发无奈起来,“我沐浴你在外面听着,这成何体统,京城里的才女都如你一般没有规矩吗?”
她话里不带训斥,反而有几分宠溺,宋暮云眼睛愈亮,从被子里伸出双手,勾住姜谣的脖子,神色却愈发可怜兮兮的,“旁的姐姐定是极有规矩的,但我现在只是罪臣之女,已经不是什么闻名京城的才女了,我进过乐坊,也伺候过贵府二公子,日子过的比莲子心还要苦,难得有人说会护着我,我怕你不见了嘛,万一这是我在做梦呢?若醒来你不在,我会吓哭的。”
说到最后,她已然多了两分真情实感,那眼睛霎时又氤氲上水汽,雾蒙蒙的,听到前面,姜谣都只有疼惜的情绪,直到她作出一副要哭的样子,姜谣立马坐直身子,妥协,“好好好,你若这般放心不下,就在外面听着吧,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值得你哭。”
女子的眼泪何其珍贵,怎能随意哭来哭去的?
宋暮云听她答应,心里难过的情绪瞬间消散,嘴角下意识上扬,露出个清浅乖软的笑来。
这会儿子又笑起来了,倒显得方才那要哭不哭的模样是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