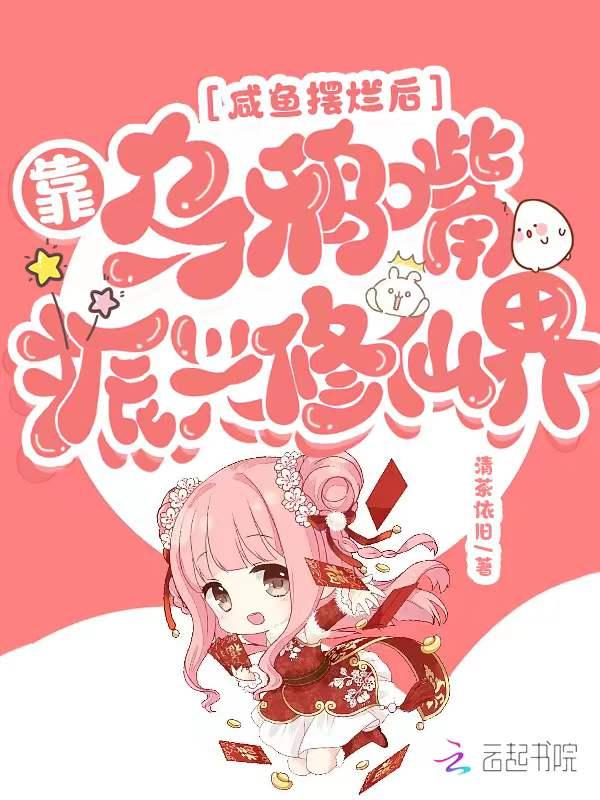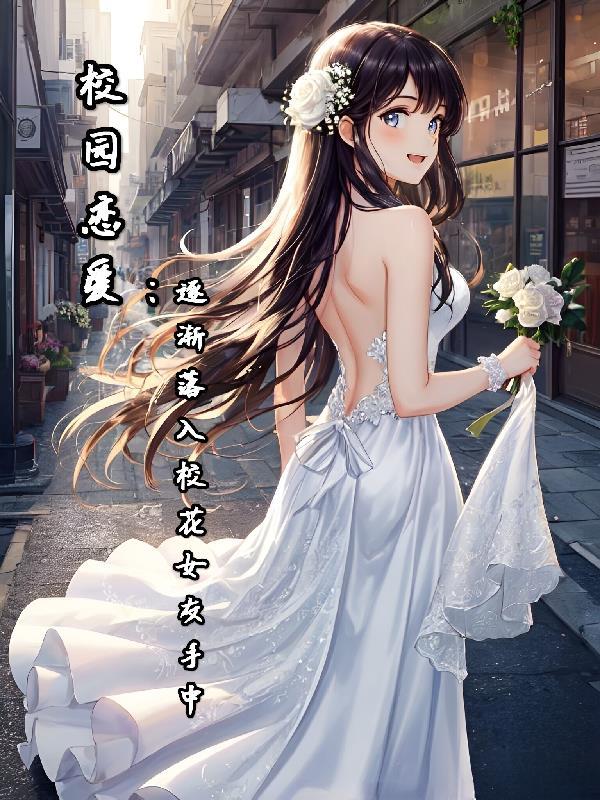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宗妇 > 第 53 章VIP(第2页)
第 53 章VIP(第2页)
张嬷嬷朝身后瞥一眼,自有小丫头上前将东西接了。
她却不忙走,站在天井里头打量着面前臊着脸赔小心的婆子们,“你们都是府里的老人儿,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不知道?主子的事是你们能编排的?大奶奶抱恙,这府里就没人治得了你们?”
“妈妈哪儿的话,如今谁不知道,是二奶奶掌家。管事们早吩咐下来,叫尽心听差服侍,适才是我们几个失言,往后再不敢如此。”
“是呀,往后再不会了。”
杏香坞建在湖对面,与蓼香汀隔水相望,距离外院甚远,其后就是老夫人住的佛堂。
这里从前是老侯爷的一位姨娘和女儿住的地方,这几年一直空着,祝琰嫁进来之前,曾翻新过一回,这回葶宜迁进来“养病”,陈设都是新置的,依照着菀香苑的规制,装饰得富丽堂皇。
葶宜躺在碧蓝织金的锦被上,脸色泛白手脚生凉,刚发过一次脾气。
她的贴身侍婢被拦在院子外不许进来。
她在屋中大喊大叫,砸了好些个杯盏碟子花瓶,那个“医女”又聋又哑,只知道木着脸不说话。身边的两个嬷嬷又胆小怕事,一味的叫她忍。还要怎么忍?她堂堂郡主,王府嫡女,都被欺负成这样了,还忍?
“你们这般行事,不怕我告诉王妃娘娘吗?王爷和王妃要治罪,只怕就连二爷也保不了你们!”
祝琰和张嬷嬷到时,几个侍婢正与守在杏香坞外头的守门婆子“说话”。
张嬷嬷含笑上前,“水仙,芍药,是你们啊。大奶奶抱恙,你们见不着人,定然很着急,这心情咱们都能明白。可是连周太医都说了,这病会传染,你们要是进去,可就一时出不来了。大奶奶身边有宁嬷嬷她们陪着,又有医女照看,我看,你们还是安心等着大奶奶休养好些,待病情稳定了,再进去探望不迟。”
婢子恼道:“你们这与囚禁奶奶何异?就连我们这些人,也被拘在府里,连门都不准出……”
“这就奇了,你们这不是好生站在这儿跟我大呼小叫吗?什么时候拘着你们了?”
她边说,边朝守门婆子摆摆手,婆子开了门,祝琰一言不发,朝内走去。
侍婢大声道:“奶奶什么时候得了重病,连我们这些身边服侍的都不知道,把人关在这里头,不许人瞧,二奶奶却怎么进去了?你们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是为了我们好,大奶奶是什么人,是你们能欺辱的?回头王爷跟王妃知道,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交代!”
“没规矩!”身后一声厉喝,打断了婢子的叫嚷。
回过头来,见数步外站着嘉武侯夫人,陪在她身侧的,竟是郢王妃。方才出声喝止她们的,正是王妃身边的嬷嬷。
“一个二个在这里大呼小叫,何处学来的规矩?二奶奶身边的老嬷嬷,是你们几个小丫头能顶撞的?方才你说什么,什么事要跟王爷王妃交代?”
侍婢怯怯瞥了眼嘉武侯夫人,嗫嗫道:“没有、没有……”
张嬷嬷回身行礼,道:“二奶奶听说大奶奶食不下咽,特地命小厨房做了几样她平素最爱吃的东西送过来。”
嘉武侯夫人点点头,“听说葶宜不肯吃饭,我也跟着担心。这孩子性子急躁,最是受不得拘束。待会儿王妃见了,还请好生劝劝。”
婆子开了门,请嘉武侯夫人等入内。
雪月将食盒里的东西一样样摆在小几上,祝琰站在炕前,低声劝葶宜,“嫂子也要顾着自己的身体,再这样下去,恐怕要熬出病来。”
葶宜侧坐在炕上,闻言抬眼看她,“你知道我没病?你知道我没病还敢把我关在这里!”
她拍了下桌案,嗤笑一声,“虎落平阳被犬欺,我赵葶宜,竟有一天会落到你手里,真是好笑。”
祝琰并不理会她的讥讽,垂眸拈起一只酒酿丸子,“嫂子多少吃一点,厨上做的都是你素来喜欢的。”她捧着碗,递给葶宜。
葶宜一抬手,把她手里的碗碟挥落。“别假惺惺来猫哭耗子,我饿死了,岂不正衬了你的意?你不是早就巴巴盼着能接替我的位子掌家?”
祝琰笑了下,“我从没想过要与嫂嫂争抢什么,至今府里公库的大钥匙还挂在嫂嫂身上,不论是我,还是母亲,从没想过要排挤嫂嫂。嫂嫂您何必多心……”
她话音未落,葶宜挥手就把身畔的小几掀翻,碗碟杯盏砸了一地,祝琰退后几步,红了眼睛,“嫂嫂……”
葶宜站起身来逼近她,“少跟我假惺惺的装模作样,祝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宋洹之定然跟你说了,说我叫人弄死了你肚子里贱东西是不是?他有证据吗?”
祝琰退后几步,摇头道:“嫂嫂你说什么?我肚子里的孩子……”
葶宜瞧她捧着小腹,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含笑向前踏出两步,按住了她的肩,“不过是个生不出来的贱种,有什么好可惜的?别说宋洹之如今没证据,就算他有,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我爹是堂堂亲王,我伯父是皇上……”
她这句话没能说完,猛然被身后一个人揪住手臂,回过身去尚未看清来人,脸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掌。
“啪”地一声脆响,所有声息都跟着静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