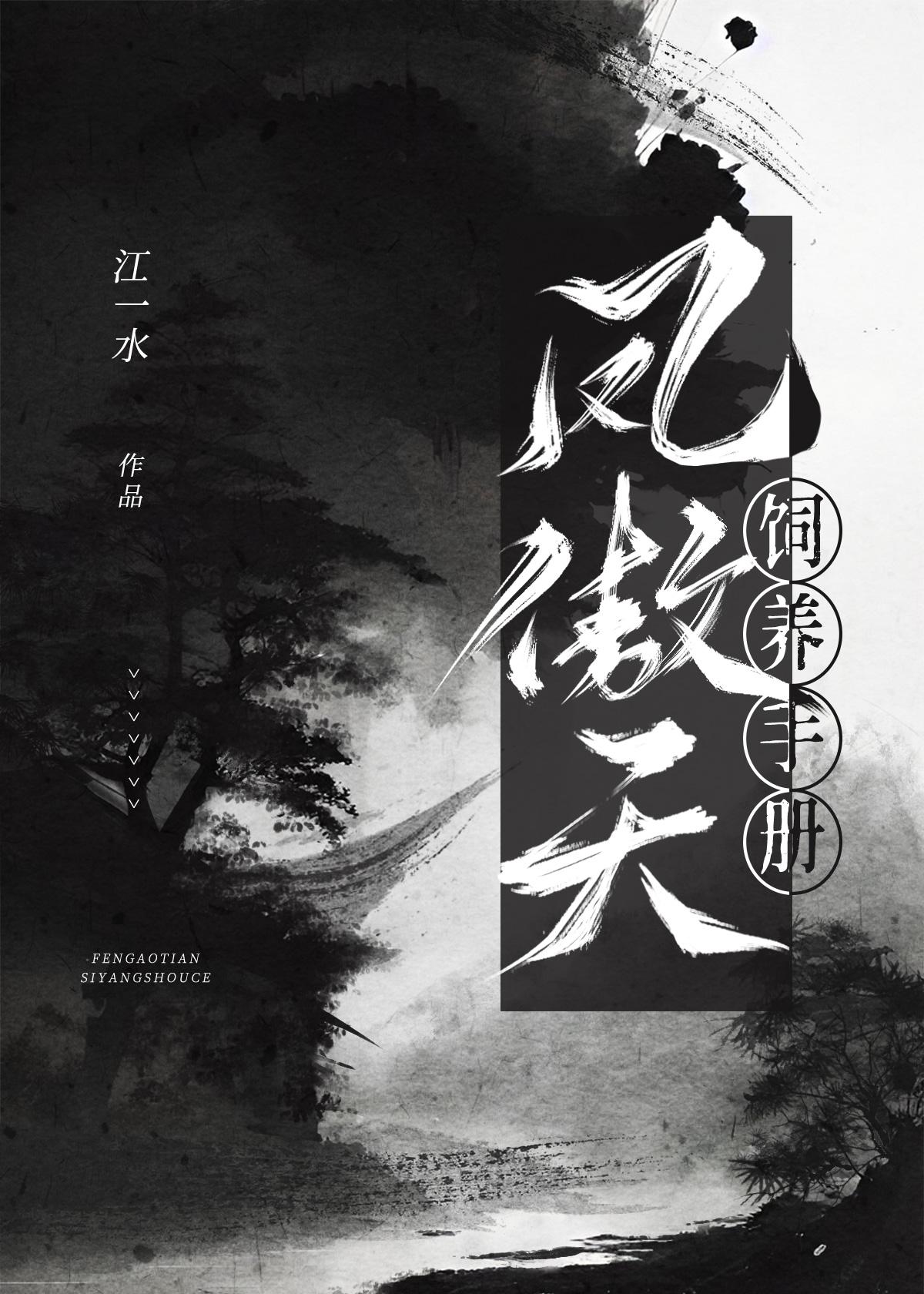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我是大明瓦罐鸡 > 第527章 又来了(第1页)
第527章 又来了(第1页)
在新城的议事厅内,气氛显得格外凝重。傅雨兰、陆青叶和任果三人围坐在一张宽大的木桌旁,正全神贯注地商讨着居民搬迁这一棘手事宜。搬迁,绝非易事,它犹如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谨慎对待,容不得丝毫马虎。
首先,对于那些准备跟着她们一同离开的百姓,新城官方需要做到事无巨细,将所有相关事宜都向百姓解释得清清楚楚。就拿百姓在新城那些无法带走的房屋、田地来说,官方必须要将其精确地折合成银两。毕竟“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古训时刻提醒着她们。若是在统计过程中稍有疏忽,未能做到公平公正,那么之后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头疼的大问题。每一户人家的房屋大小、田地肥瘦都不尽相同,要想给出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折算标准,就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走访、丈量、评估,每一步都必须严谨对待。
再者,便是抵达目的地之后的住宿问题。众人心里都明白,如今扶桑那边的生存条件相较于新城,着实差了不少。百姓们一旦到达那里,在短时间内,生活质量肯定难以得到保障。倘若不事先将这些情况跟百姓说清楚,便贸然将他们带过去,一旦百姓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必然会惹起民怨。这民怨一旦积累起来,就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她们不仅要告知百姓那边的现状,还得提前规划好临时安置点,以及长期的住房建设方案,让百姓们心里有底,知道未来的生活虽然会面临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
像这般繁杂琐碎的问题还有很多,自从朱高煦离开后,陆青叶、傅雨兰和任果等人便全身心投入到商讨之中,一晃眼已经过去了好些天。然而,毕竟这是她们头一回处理如此庞大且复杂的工程,对于其中诸多事务,几人都显得有些生疏。尽管她们都深知此事责任重大,却也只能边摸索边推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应对。
在这几日的时间里,几个女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已经商讨出了不少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是她们反复权衡、激烈争论后的成果。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她们又不断发现许多不合理之处,然后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前前后后已经改过好几处了。她们心里都清楚,朱高煦将这件关乎众多百姓生计的大事放心地交给她们,是对她们的信任,而她们也都一心想要把事情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所以,这几天她们几乎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常常是天还没亮就聚在一起商议,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各自回房休息。
此刻,正当三人专注地商议着如何更有效地将百姓分批迁移时,突然,一名侍女神色匆匆地快速跑了进来,在门口停下,双手撑着膝盖,气喘吁吁地说道:“几位夫人,刚刚得到消息,有人在新城城门口发现了燕王的身影。”
原本还沉浸在激烈讨论中的三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伏在桌子上勾勾画画的动作瞬间定格,然后同时抬起脑袋。她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大门口的侍女,一时间,整个房间陷入了沉默。
就在侍女满心疑惑,实在不解三人为何露出这般表情之时,陆青叶先是嘴巴微微一撇,而后慵懒地将原本搭在桌子上的衣袖耷拉下来,整个身体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般垮了一些,嘴里更是不满地嘟囔起来:“他怎么又来了?”那语气中满是厌烦,仿佛燕王的到来是什么无比扫兴的事。
听到陆青叶这话,旁边的傅雨兰差点没憋住,直接笑出声来。她好笑地看着陆青叶那一脸郁闷的表情,心里暗自想着,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哪有儿媳这么嫌弃自己公公的,听起来就好像燕王是个特别招人烦的玩意儿似的!
毕竟每次朱棣来到新城,确实都没安什么好心,就没见他做过几件纯粹利人之事,每次离开的时候,那可都是把好处揽了个精光。再加上前几日发生的一些事,朱棣的行为和陆青叶产生了一点小矛盾,这才使得陆青叶一听到燕王的消息,就表现得如此烦躁。
不过,人家朱棣毕竟是燕王,更是朱高煦的亲生父亲。她们几个人身为朱高煦的老婆,即便心里对燕王有再多不满,在表面上也绝不能表现出来。所以,傅雨兰赶忙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陆青叶的手掌,一脸认真地说道:“青叶姐姐,可不能这样说话呀!咱即便心里有想法,也得注意分寸,别让人挑出理来。”
陆青叶也明白自己刚刚有些失态了,心里清楚傅雨兰这是在为自己好,便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见陆青叶听进了自己的劝,傅雨兰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将手中的资料整理一番,把散落在桌上的笔也规规矩矩地放好位置,而后缓缓起身。她一边轻轻掸了掸裙摆,一边开口说道:“既然燕王已经抵达,咱们还是出去迎接一番吧。话说回来,除了燕王,还有谁一同前来呢?”傅雨兰心里跟明镜似的,朱棣挑这个节骨眼来,肯定又是打着捞好处的主意。但不管怎么说,人家燕王身份尊贵,该给的面子还是得给足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那侍女从进来通报消息后,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没敢离开。听到傅雨兰的问话,赶忙上前一步,恭敬地回答道:“听前来上报的人说,此次只看到燕王和燕王妃两人抵达新城。至于暗中还有没有其他人跟着,这就实在不得而知了。”
听到侍女这样说,傅雨兰不禁长长地松了口气。心想燕王妃一同前来就好,燕王妃向来是个有分寸的人,做事不会太离谱,有她在,或许能稍微约束一下燕王,避免场面太过难堪。
“行了,你退下吧!”傅雨兰轻轻挥了挥手。待侍女离开后,她略显疲惫地揉了揉眉心,转身对着陆青叶和任果两人说道:“咱们先去清洗一下,整理整理仪容,然后前去迎接吧。”
“好的!”任果向来行事利落,立马干脆地起身应道,而后快步朝着自己房间走去,准备稍作收拾。
陆青叶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但也明白明知朱棣前来却不去迎接,那就是自己不懂礼数了。况且燕王妃也一同来了,说不定燕王妃能帮忙周旋一二。这么想着,她虽有些别扭,但还是朝着自己房间赶去,准备收拾妥当后,与众人一同去迎接燕王夫妇。
而此刻,朱棣和徐妙云正站在新城的广场之上,脸上满是目瞪口呆的神情。原本二人计划着径直前往城主府,可当他们目睹广场上的场景后,双脚仿佛被钉住一般,再也挪不动了。
眼前的广场,南北两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犹如楚河汉界般泾渭分明。广场北边的边缘,赫然矗立着一处巨大的高台。高台之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壁背景板,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许多字迹。背景板前方,早已围得水泄不通,百姓们摩肩接踵,一个个交头接耳,嘈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台上,有几个看起来像是新城工作人员的男女,正滔滔不绝地对着百姓解说着什么,他们时而指了指背景板上的内容,时而又用手势比划着,似乎在向民众传达着某些重要信息。
再将目光投向广场南边,只见几个粗壮的大柱子突兀地矗立在拐角处。柱子上,绑着几个低垂着脑袋的犯人,他们浑身布满了伤痕,血迹斑斑,看起来毫无生机可言,仿佛生命的气息早已从他们身体里抽离。在柱子前方,同样站着上百名书生模样的人。这些书生个个风尘仆仆,显然是经过了长途跋涉。尽管他们谈笑风生,但脸上仍难掩疲惫之色。他们正对着柱子上的尸体指指点点,时而发出几声叹息,时而又低声讨论着什么。
朱棣的目光一触及石柱上的犯人,嘴角便忍不住狠狠地抽了抽。虽说这是他首次亲眼见到这般场景,但之前从探子口中,他早已听闻过此事。若是猜得没错,柱子上绑着的,应该就是自己当初偷偷交给朱高煦的那些曾经的官员。他心中暗自感慨,没想到这些人即便死了,也还要被朱高煦如此处置,挂在这里任人围观、凌辱,死后都不得安宁。
好在这些犯人个个蓬头垢面,脸上满是污垢与血渍,根本让人看不清他们原本的面貌。否则,若是让北平的那些官员知道这些昔日同僚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那还不得像热油锅里滴了水——炸了锅啊!北平官场势必会掀起一阵轩然大波,说不定还会引发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应该就是刚从高丽赶回来的那些学子吧。”徐妙云的目光落在那些书生身上,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赏之色,声音轻柔地在朱棣耳边响起,“你瞧,他们虽然身上的衣衫破旧不堪,皮肤也被晒得黝黑,可那精神头倒是相当不错。而且啊,他们的眼神灵动,透着一股朝气与聪慧,比起那些整日只知读死书的北平书生,可要鲜活、强上不少呢。看来,战场果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啊!”
实际上,朱棣在看到石柱上的官员后,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便将目光迅速转移到了书生们的身上。毕竟,既然已经把那些官员交到了朱高煦手中,对方要如何处置,自己确实也不便过多干涉。此刻听到徐妙云的这番话,朱棣深有同感,不禁赞同地点点头,目光中满是对这些年轻人的认可与满意。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赶回来了,老二办事倒是利索。”朱棣心情大好,想到朱高煦将此事处理得如此干脆,忍不住夸赞了一句。言语之间,对朱高煦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本来呢,朱棣早就在心里盘算着前几日就动身前往新城。他心里惦记着新城那边的诸多事务,想着去看看朱高煦把新城经营得如何,说不定还能从里面捞取一些好处。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他刚准备打点行装、启程出发的时候,还没等他迈出北平城,新城的人就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北平。
抵达北平的人,是石当特意派来的。这人一路快马加鞭,风尘仆仆,只为了向朱棣传达一件事,那就是让朱棣赶紧对接港口的船只。原来,此时的港口已经人满为患,聚集了不少心急如焚的商人。这些商人的货物堆积如山,都眼巴巴地等着船只运输呢。每耽搁一天,他们就损失惨重,而对于港口来说,尽快接手这些货物运输,一天就能有大量的白银流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崽崽们亲妈是万人迷[穿书]](/img/467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