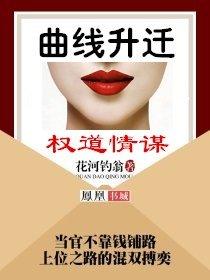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冷宫种菜,带飞太子 > 第122章(第2页)
第122章(第2页)
如往时一般,容璧和元钧很早便熄灯上床,容璧睡在内,元钧在外,却除了那一夜,一直十分守着君子之礼,衣不解带睡在一侧。
容璧开始还觉得有些羞赧,但后来却渐渐习惯了这种相濡以沫一般的安静。
这夜她闭着眼睛躺在内侧,闻着身侧太子身上传来的丝丝缕缕的沉香味和匀长的呼吸,也早早就睡沉了。
而在深深的荷池下的密道里,之前刚刚填上了一半的密道,已又被重新挖开了来。沈安林带着一群穿着东宫侍卫服的精干侍卫,从密道中鱼贯而入,在东宫侍卫后,是另外一群穿着玄甲的精悍兵士,全都佩刀森然前行,这么多人在狭窄密道内,却一丝声音都没有。
荷塘上的水榭内,盖子忽然被从内推开,东宫侍卫们犹如幽灵般悄无声息地从密道内钻了出来。
沈安林带了四个平日经常值守的东宫侍卫走出了水榭,提了灯,从桥上大步走向对面禁卫的值日房。
荷塘边站着的青犼卫已立刻发现了九曲桥上有人,大声喝道:“什么人?”
沈安林沉声道:“是我。”
青犼卫有些诧异,听着耳熟,看着对方提着灯穿着东宫侍卫服,有些诧异,等人走过来近了看到是沈安林,下意识行礼道:“沈统领。”
沈安林微微一点头:“辛苦了,不是说今天于统领晋升请吃饭么?你怎么没去?”
那青犼卫满心迷茫,沈统领不是告假吗?什么时候又进来了?但仍然服从着平日里的面上情:“值夜班呢,等换了班就去。”
沈安林微微一笑:“那我先过去贺一贺于统领了,这可是难得的喜事。”
青犼卫看着沈安林大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灯也往前去了,桥上重新归于黑暗,禁卫忽然想起一事上前有些茫然提醒道:“沈统领,宝函宫已落钥了不能进出了……”他转过身,却没注意到沈安林背后的东宫侍卫在他身后举起了刀,手起刀落,用刀背敲晕了他。
九曲桥上源源不绝从里头奔出了一队一队的士兵,训练有素地在黑暗中形成了队列,一队抽刀迅速向熟悉的岗哨边奔去,另外一队跟着沈安林到了值日房里。
沈安林走入值日房里,看里头的禁卫正闲着摇骰子玩,然而却也不敢大声吆喝,看到沈安林带着穿着盔甲的兵丁进来,手持利刀,全都赫然站了起来按刀。
沈安林挥了挥手微微一笑:“都是兄弟们,看在素日的情分上,弃刀不杀,若是顽抗,来日我会为诸位兄弟们祭祀的。”
青犼卫的暗卫们看着这一群数倍于自己的执刀披甲的悍然精兵面色骤变,再加上窗口打开,那里密密麻麻数位满开长弓的甲士,都知道无力回天,只能纷纷弃了刀,然后被捆了手足堵了嘴蒙了眼,连成一串关在值日房里,心中全都浮起一个问题:他们怎么无声无息地进来的?
寝殿内,容璧被元钧摇醒的时候,双眸尚且带着懵懂:“殿下,天亮了?”
元钧低头看着她,面色温和:“无事,有些事要处理,怕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你先出宫去,孤已安排了人送你出去,你两位哥哥都在外边接应你,也不要回小院了,你去公主府,好生歇着。”
容璧起身茫然看向窗外,窗外仍然漆黑一片,白缨和红缨过来服侍她披上了一身玄黑色的兜帽氅衣,为她着靴,和平日所著的裙袍绣鞋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