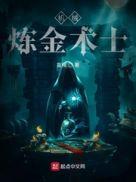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野心臣 > 第196章(第2页)
第196章(第2页)
我将萝藦在手中打转,凝眉细观,肆意把玩后,一子落入,洛桑的满盘皆落索。
他懊恼地挠了挠头,向我一挑眉。
“看来我的追击之日,还漫长。”
我得意地抱臂弯轻笑,莫名觉得此句别有深意。
“知道就好。”
洛桑忽然复念《芄兰》的后半句,眸光从地上随意画出的棋盘抬起,从一败涂地的棋子上扬起,深深望我。
“虽则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带悸兮。”
我心恍然,似乎刹那置身那日卧斋听雨,绵绵青烟,隔着重重雨帘,雨水下得一塌糊涂,与我执棋者不再是张怀民,而是笑意浅荡的洛桑。
我眉眼怔忪,念起那日的春雨入骨暖酥,终是再次落上我的肌肤,清凉而心悸,触感真实到我疑心是在梦中。
我先摸了摸脸颊,又抚上洛桑的脸颊,我们温度那样贴近,这一次,降雨者,不是天公作美,而是洛桑使然。
我陡然醒悟这就是真实,而非自作多情的梦境,于是不好意思地望向自己停留在洛桑脸颊的那只手,拿开也不是,逗留也难堪。
正当我进退两难之际,洛桑轻缓地握住了我意欲逃离的手腕,将我拽得离他更近,轻轻笑了。
“萝藦繁茂,我未见君及笄之年,可是又如何呢?”
我愣住,良久莞尔。
“萝藦生果,我未见君冠礼之年,因为君在西戎。”
知我如此,不可无生
我忽觉拉得过近的距离,于是心不在焉地揽了揽衣袖,极不自然地别开视线,而洛桑热烈的视线未减退半分,而是生生笑道。
“阿依慕,这是怎么了?”
我语塞,嗔怪地瞥了他一眼,没好气道。
“气你又在我面前抖机灵。”
洛桑躺着也中枪,于是捂住心口一副心痛的模样叹息道。
“啊,被阿依慕嫌弃了,洛桑我好难过。”
我闻言脸上一阵燥热,面色刻意变得冷淡些,可是在真正松弛的状态下,人眼底的平和是难以掩藏的。
另外,在将你认真放在心上的人眼里,你气鼓鼓的另一面,他也来者不拒。
我讥诮地勾起唇角,陡然给他使绊子,随意指着地上的不知名草儿目光锐利。
“既然你声称自己熟知中原诗经文化,那么,我倒是很期待洛桑老师的课堂。”
洛桑丝毫没有气馁或退缩的神色,爽快应下,拍着胸脯道。
“没问题,阿依慕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