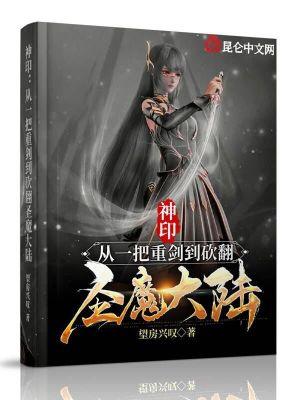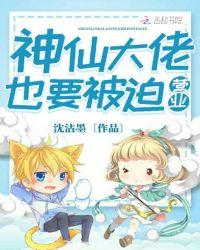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三国]在全员美人的家族做谋士 > 第165章 第 165 章(第2页)
第165章 第 165 章(第2页)
大太阳底下,益州牧身上所着的蜀锦衣物华美而繁复,细密的金丝银线几乎能晃花人的眼睛。
他生着一张一看就是好脾气的脸,略微有些发福,在众人的簇拥下也没有太大的威势,他亲自迎二人进城。
待得入宴会席中时,已不知过去了多久,荀晏忍耐着浑身不适,抬眼望去,满座皆是陌生的面孔,那是益州的官员们。
如何劝说,如何分析,一路来心中早已打好了腹稿,只是如今还得在这宴会上推杯换盏。
无形的交锋在酒桌上完成,这似乎已经快成了个习俗,就连隔绝于世的巴蜀也是如此,酒盏轻轻举起,只略微湿润了些唇便放了下去,荀晏有些头疼的漫无目的的想着。
刘璋似是早有向曹操示好之意,此时也顺水推舟,笑道:“海内大乱,社稷将倾,璋虽拥巴蜀之地,却只能安坐于此,曹公率义兵为天子诛逆,功高德广,璋岂敢不从。”
席中诸人或是冷漠或是不满,亦或者是欣喜,各异的眼神从上位那年轻的御史身上滑过,众人窃窃私语着,最终仍是没有人提出异议。
刘璋如此表态,荀晏亦不可无所作为,他顺势起身,举杯而道:“刘公大义,当为天下楷模。”
说罢,他一饮而尽。
刘璋笑意真诚了一些,当堂讨论了起来该如
何用兵,该发多少兵马。
荀晏坐下后只觉额角一顿一顿的疼,冰凉的酒液入喉,带起一阵灼烧般的麻,他有些神游的望过堂上诸公,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棘手。
此行虽是顺利,但依他看来,其中许多人仍然持中立之态,并不倾向于曹操,如今愿意出兵很大的可能却是看在以荀攸为主的亲曹派上。
昔年刘焉入蜀,扶持出了以南阳三辅人为主的东州派,经过父子两代经营已是盘根错节,甚至压制着益州本地士族。
而公达入蜀后拉入了部分的颍川士人,对比起来仍然不成气候,但他斡旋于其中,左右逢源,今又取五斗米道,已硬生生拔出了第三只势力。
自古权衡主客最是困难,益州的现状,不论是东州派还是颍川派,皆是外来之客,那些自刘焉一代起就一直被压制的益州士族又是什么想法呢?
底下的士人看着情形,嘴角笑意愈重,只是眼底却心绪难测,不一会便有人上前来敬酒。
“素闻颍川荀氏多良才,昔日见荀公,今又见御史,方知名不虚传,不知御史可有意多留一些时日,观我巴蜀之河山?”
那人笑吟吟说着,也不知是玩笑话还是什么,荀晏记得这人,此人正是中郎将吴懿,刘焉领益州牧时,此人率全家跟随入蜀,可以说是老刘家的家底之一了。
“吴中郎善相面之术,”有人同样在席间笑道,“昔日有善相者道中郎之妹后当大贵,可惜其夫早逝矣。”
席上一时冷了一瞬。
他这话看似没什么问题,却一时之间打到了一堆人。
无论是所谓‘后当大贵’的吴懿之妹,又或者是娶妻吴氏,早已在权位争夺中去世的刘焉三子,如今刘璋的兄长,刘瑁。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